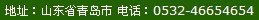|
中科医院专家 https://mip.yyk.99.com.cn/fengtai/68389/zuozhen.html 年1月20日,澎湃新闻市政厅与第12届上海双年展合作发起的城市项目“你的地方”的第一场平行活动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进行。 借由自己的工作成果,四位影像工作者分别回答了对在上海的“迁移者”这个命题的思考。这其中不仅包括新上海人,外来务工人员以及他们的子女,还包括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不得不在地理位置上平移的老上海人,在上海开店很多年后回老家的店主,人走屋空后留下的流浪猫狗,以及许许多多与我们擦肩而过的人。通过影像创作者的眼睛,我们更长久地注视彼此。以下为本次活动部分文字节录。 贾茹:我和外来务工子弟活动中心的缘分 今天很有幸来到这边,跟大家享一下我作为一个新闻摄影工作者,这些年拍到的为上海外来务工子弟开办的 久牵志愿者服务社 的一些影像。 我第一次接触久牵是在年。先说我和久牵的缘分,八年间的四次拍摄和那九个孩子。“孩子”这个称呼,就好像我是一个大人一样。我第一次接触久牵的时候,我自己是一个研究生。那个时候我跟他们普遍的年纪应该差六到八岁之间。 这九个名字,以时间顺序来讲,是年的何世丽,年的 武子璇 ,年的林创创、王欢、郭静怡、苏童、翁宇、班富俊、丁莹鑫。 这九个人都来自久牵。我觉得,他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有很大差别。就像武子璇说的,他们有的人做的选择是父母做的选择,他们可能是随波逐流。有的人做的选择是他自己的选择,而他们选择超出他们父母的预期。而这个选择直接影响到了他们今后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我接触到的久牵的学生,不止他们九个人。有的已经工作,有的已经结婚生小孩,有的已经离婚了。 久牵很神奇的一点就是,离开久牵的孩子,包括因上世界联合学院,去加拿大,去美国读书的孩子,在暑假和寒假的时候,都会回到久牵。他们依然跟这个地方保持着联系。就是他们好像在一个流动的大楼里面找到一个定点,通过这个定点跟这个地方发生一个深刻的关系。 我年拍摄的第一个学生,叫何世丽。她其实是最早和武子璇做出了一样的选择。我记得她跟我说,她母亲生第三个小孩的时候,小孩流产了,身体不好,她跟母亲回到了四川老家。她现在在读一所大学的护理专业,没有毕业。这是她当时住的地方。 何世丽澎湃新闻记者贾茹图 何世丽年在上海的居住环境澎湃新闻记者贾茹图 我跟她一起在这里住了两个星期。城市里面的农田,尤其上海城市里面的农田,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那个时候的邻居,就是像林创创说的,就是街上的环卫工人什么的,有小孩,有狗,可以洗衣服,可以种地,有点不像上海,像是另外一个村庄。 当时久牵的张轶超老师来他们家家访,跟她的父亲谈,问到底要怎么选。因为中考的时候,他们几乎全部的人的父母,都达不到上海居住证的关于随迁子女中考的标准,所以他们必然面临的一个选择就是,是留在上海念中专、放弃高考,还是回到老家参加高考。 我为什么想要拍他们?公益组织有很多个,我当时接触到久牵,是因为我们导师带我们跟上海的公益组织都兜了一圈,跟很多人接触。久牵当时的学生给我的印象是,我感觉不到他们身上那种应试教育的压抑的氛围。我感到一种很新鲜、很自由的东西。可能那个东西把我吸引了回来。当时我已经离开了上海。过了差不多半个月,我又下定决心,我想回来看看,为什么这个服务社的孩子是这样的。所以久牵的宗旨,就是自由的探索,自由的表达,自由的创造。 我觉得在武子璇身上,钢琴可能给她留下了印记。或者说,任何一门课都会这样。他们在久牵上的钢琴课、哲学课、历史课、逻辑思辨课,这些东西在一个正常的高中里,尤其是要接触高考的高中里,我觉得都不是常见的课程。这些东西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很自由的东西,很新鲜。我见证了他们人生中的一些关键的选择,而久牵让他们多了一些选择。 当然,久牵之外还有一亿个名字。这个数据来自《风中的蒲公英》(上海文化出版社,年出版),这本关于流动儿童的书里,陆铭教授的文章。这一亿儿童包括数量超过六千万的农村留守儿童和数量超过三千万的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两者加在一起的量就在一亿左右,占全国儿童的三分之一。 作为一个观察者,我觉得有机会接触到久牵,是某种程度的幸运。 扫码支持久牵志愿者服务社“蕙兰的绽放项目” 施佳宇:老西门的小生灵 我在大学里刚开始拍照的时候,喜欢拍城市的风光,会跑到高楼上去,获得更多的拍摄角度。毕业之后,我进入了一家上海的建筑公司,那家公司专门造高楼。而我接触了两个项目,一个是厂房,一个是地铁,跟高楼都没有关系。 后来,我进入了徐汇区一家历史建筑修缮公司,专门跟老房子打交道。从那时开始,我也慢慢地对上海的老城厢、一些老的建筑开始感兴趣。年年底,我开始跑到老西门去拍照。 其实三年前我去过一次老西门,那时候还没有动迁。动迁的消息一直有,十年前就有,消息一直在那里,一直没有动成功。三年前那里还很热闹,人和人之间走路都很拥挤。那个时候没有拍,现在挺后悔的。 动迁以后,很多地方都“敞开”了。有些人也愿意吐露自己,展现自己,他们也觉得这个地方应该用影像留下来。我从年年底到现在,总共拍了一年多的时间。 《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下册第37图 这张图刚好就是现在老西门动迁的那块区域。中华路、方浜中路、松雪街和复兴东路围合而成的这片区域,年年底,第一批开始动迁。 我把老西门当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项目去拍。我当时的期待就是,我想把老西门(拆迁)整个过程都拍下来,拍得面面俱到,甚至要绝对的客观、绝对真实的记录。后来发现这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老城厢里面经营着很多的烟纸店。我的感觉,不是为了盈利,而是因为一年一年开下来,他们不想有什么变化,早就习惯了。烟纸店像大家交流的中心,大家喜欢聚在烟纸店前聊聊八卦,也聊聊其他事情。 飞飞烟杂店施佳宇图 跟我故事最多、关系最深的一家店,是在金家坊号的“飞飞杂货店”,这家店的主人还有他们的孩子今天也都来了。这张照片是他们家的猫、外婆,还有小妹妹。 我从《上海市行号路图录》里考证了一下,号在地图里没有记载,但那时的号和号都是杂货店。 这家店最有意思的就是,他们的两个小孩子跟我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我知道他们家要搬的时间了,一直想给他们拍个全家福。 那天去他家之前,我在脑子里想了很久,要用胶片,要足够地郑重,给他们家里拍一张足够好的全家福。我觉得,拍全家福的那个时刻应该是很神圣的时刻,我想了好久,各种各样的版本。 飞飞烟杂店全家福施佳宇图 后来那张全家福很短暂就结束了。因为哥哥和妹妹根本就没有耐心拍,哥哥在做鬼脸,妹妹那个时候已经没有耐心了。很有意思,这样的照片很真实,不一定大家的表情都要很到位。 飞飞烟杂店的最后一天施佳宇图 在他家搬走的前一天晚上,算是一个告别。那天下着雨,我还是到他家玩了两个多小时。哥哥和妹妹可能对搬家没什么概念,我知道,外婆在那天晚上应该是很不舍的。外婆那天话不多,哥哥和妹妹在那里疯(玩),(外婆)有时候理理东西,有时候坐在那里发呆。我觉得可能外公和外婆是在这里生活得最久的人,她可能会想起以前带女儿,带儿子,现在看到外孙、外孙女,会想到以前的一些事情。 飞飞杂货店搬家的第二天施佳宇图 第二天他们家的东西全都搬走了,垃圾什么的都扔掉了,妹妹还是很好奇地回到了店里。我觉得这张照片有一点伤感,外婆看着外面,妹妹在里面寻找着一些东西。后来搬出来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都是她舅舅小时候的玩具。这是我给他们在老西门拍的最后一张照片。 后来我和妹妹以及她的妈妈也加了
|
当前位置: 徐汇区 >你的地方实录迁移者之地日常生活中继续前
时间:2022/8/9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2021年徐汇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
- 下一篇文章: 六五环境日优化营商环境,徐汇生态环境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